应好友、设计师何见平之邀,参加2023年Design Summer的演讲稿
命运的中场休息
文/春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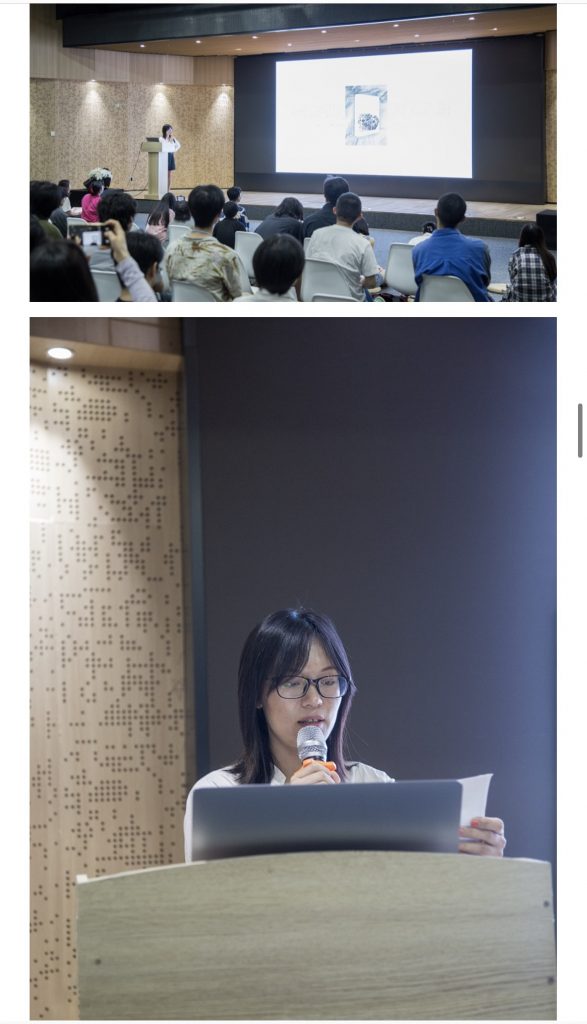
重回母语世界
“回国前几天,我就开始焦虑,既期待又焦虑。我害怕,具体害怕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只是隐约感到恐惧。我想起移民加拿大的哥们儿Wave说的,他每次回北京之前也会焦虑好几天。想到这点,我好了一点。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啊,那就好了,我的反应还算正常。
一上飞机,我的心就定了。四周坐满黄面孔的国人,我像已经提前回到了中国。飞机上,宝宝睡着了,小手还放在我的手里。我用一只手给他盖上一条毯子,过了一会儿,也给自己盖了条,想了想,又把我的毯子也盖到他身上,给他仔细掖了掖,不知怎的,我就产生了一种俺们娘儿俩相依为命的感觉。
飞机从柏林的泰格尔机场,跨越欧亚大陆,直飞到北京。”
这是我的小说《乳牙》第一章里的开头。现在泰格尔机场已经废弃了,改成了另一个机场。
这次回国,宝宝坐在我的右边,他已经快八岁了,他一直在看旁边女孩屏幕上的儿童电影,因为我们俩的屏幕都不太好用。这一路长达9小时55分钟,很意外的是,我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漫长,就像我以往一样。以前我坐长途航班回国,总是觉得非常漫长,不知道时间该如何打发。我是个在飞机上什么事都干不了的人,不但没法写作,甚至就连书都看不进去,最多翻翻报纸杂志。我突然意识到,会不会是因为宝宝在我身边,我的心很定,这让我感觉踏实,因此时间也就不再那么重要,或者说时间不再像被拉长了一样难以忍受。后来他睡着了,我给他掖了掖毯子,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乳牙》的开头。相依为命的感觉再次笼罩了我。这次,我感觉到了安心。我已经五年没带他回国了,这五年发生了许多事,其中有一件很大,那就是长达三年的疫情期,这三年,并不太平,国内外都深受其害。而这八年来,我无数次地想过要回国生活,但现实条件是我很难把他一起带回来,我就在这种矛盾和彷徨中挣扎自苦,这次终于可以带他回来,看看北京,跟亲人们聚聚,对我来说是久别重逢,更像是一场中场休息,或者说是胜利。《木兰辞》里写木兰打完仗回家“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是后话。当我们两个在波兰华沙准备坐飞机的时候,我确实有种历经沧桑终于要回到母亲怀抱之感慨和欣慰。

1923年的8月,冰心由上海乘约克逊号邮船赴美国留学,8月19日抵日本神户,21日浏览了横滨,在浏览了横滨的第六天,冰心写了一首诗叫《纸船——寄母亲》,这首诗我在我的《中国当代诗歌鉴赏与写作》课程上,专门选出来给学生讲过,这首诗的最后四句是: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一个是归去,一个是归来。但归去也会再归来,而归来也会再告别。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有爱和不舍。
故乡让人如此不舍,可能也是因为这里是我们的母语区,我们文化组成的由来。有记者问我在柏林汉语写作的感受,我说,那就像在沙漠里寻找绿洲。我很珍惜地把我们的汉字拢在一起,然后用我的想象力把它们再组合起来,成为新的作品。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和那些马华作家有点类似,他们用汉语写作,也处在一个不那么重视华文的地方,但又必须要去这种文字来达成一种文化抱负。
回国前一礼拜,我去potsdam,柏林旁边的一座文化历史悠久的小城,也是勃兰登堡州的州府,去看望一位朋友,她在那里的一个大学城附近开了一家咖啡馆。上次我们见面应该还是在2019年,在等红绿灯时,她突然对我说“即使外语说得再好,也好想痛痛快快地用中文聊天啊!不用思考什么语境,也不用琢磨背景,说中文,好放松啊!”
我们这次倒是谈了很多学德语的问题,同时谈到的是生活中的定位问题。我们都特别喜欢北京,她是重庆人,但11岁就来了北京,和我一样,不是那种循规蹈矩长大的孩子,她不上班,她赖以维生的是开咖啡馆,她喜欢的是能够拥有一个场所,把喜欢的人聚集到一起。作为高敏感度人格,她说每天都特别痛苦。我说我也是。这种痛苦是我们本来的生活圈子都是搞艺术搞文学的,到了一个新国家,接触的人跟文字艺术不相关,而我们也很难融入到那个圈子,这跟语言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语言不足以让我们表达出内心真正的想法,有时候连一个幼儿园的孩子都不如。我们也只好一边补上新的语言,一边不放弃我们自己的母语。对我来说,这问题相当严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跟纳博科夫一样,拒绝学德语。其实我很早以前,对德国是充满憧憬的,真正生活起来,滤镜全碎了。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我并不缺乏交流对象。我几乎每天都会和国内的朋友聊聊天,有时候会跟诗人朋友或者作家朋友聊一下我们近期的写作或者阅读。有一个前两年总是在谈创作的朋友现在总是在说很累,要带孩子……即便如此,也总会在朋友圈看到他转发同行的作品或者自己写的文学评论。
文学场域内的交流必不可少,我们都曾受过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影响,这里包括着对写作风格及写作技巧,还有文学审美的传承和认同等方面的影响。
在文学与艺术中寻找经典形象
从作家的形象和生活上来讲,有些作家特别有魅力,而他们的生活也特别让人产生好奇心。在青春期的时候,我特别着迷于萨特的文论和小说,后来他的作品对我有点失效,但十五岁的时候,一本绿色封面的萨特作品集,一张萨特站在巴黎桥上抽烟的照片,还是能让我一看再看,并且给我一种知识份子的完美联想的。
刚开始写诗的时候,美国自白派影响过我,首当其冲就是一张Ann Sexton的照片。这张照片就像她诗的注角,一个女诗人在她的书房,手夹一支烟,直视镜头,面带微笑。其实是先看到她的诗,再看到她的照片,她的诗与她的照片,给我完全不同的想象力。
“黑色的艺术 译:倪志娟
一个写了太多感觉的女人, 这些晕眩和奇迹! 仿佛月经、孩子和岛屿 还不够多;仿佛忏悔、闲话 和蔬菜永远都不够多。 她以为她能警告星星。 一个作家在本质上是一个间谍。 亲爱的,我就是那个女人。
一个懂得太多的男人, 那些符咒和迷信! 仿佛勃起、集会和产品 还不够多;仿佛机器和帆船 和战争永远都不够地盘。 他用旧家具做了一棵树。 一个作家在本质上是一个骗子。 亲爱的,你就是那个男人。
从不爱我们自己, 甚至恨我们的鞋子和帽子, 我们彼此相爱,珍惜,珍惜。 我们的手是淡蓝色的,温柔的。 我们的眼中充满了可怕的坦白。 但是当我们结婚时, 孩子们厌恶地离开了。 有太多的食物,却没有一个人留下 吃光所有的风味美食。”
喜欢上摇滚乐后,先是听Nirvana,随后听了主唱柯特的老婆柯妮的乐队Hole,完全被她的金发红唇所迷住。我当时写了一首诗:
关于一个女人 About A Woman
柯妮——拉芙
我真是嫉妒死你了
一个美国女人
和我一个星座
在二十年之内搅得摇滚圈不得安宁
和她已自杀的老公一起成为新一代摇滚乐的国王和皇后
柯妮拉芙
我现在正在看你的照片呢
从照片上看
你穿着一身粉红色的吊带裙涂着粉红色的唇膏 拿着把吉他
气质高傲 漂亮死啦
你早就成为了我的偶像,哦不,是榜样
金黄色的头发,大嘴巴、大胸脯、大嗓门、大个子的女人
身上有伤痕
柯妮拉芙,总有一天我要去美国找你去
我们好好聊聊
我要向你介绍自己:我是中国来的一个诗人
你会不会笑我?
尤其是最近,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愈加对你尊重
所有人都虚伪,就你不
当网上那些虚拟人物一古脑儿地骂我时
我就会想起你来2001,11,7
在早期,我真的很想成为一个摇滚乐手,直到我发现我唱歌跑调,也没什么玩乐器的才华。不过我一直都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一直喜欢听摇滚乐,到了国外有时候也会去听古典音乐会。都是音乐,但他们的受众无论从打扮还是从生活方式上来讲,几乎没什么相似点。回国前我看的两场演出分别是在柏林爱乐听的马勒第三交响曲和在clash酒吧的三个女子朋克乐队的演出,其中一个来自青岛的乐队Dummy Toys的两位成员是我的好朋友。我与其中一个乐手相识于彼此的少年时期,在北京,在青岛,当时我们一起去看演出,都是作为观众。后来她回到青岛,在另一个玩乐队的朋友的鼓励下,自己也开始玩起了乐队。她们乐队的形象就是特别经典特别典型的街头朋克造型。她们中有几个已经成为了母亲,孩子跟我的差不多,但她们平时就是这个打扮,别说在国内了,就连在柏林,这么纯正的punk造型的都不是那么多了。
服饰和造型肯定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就像工人要穿工作服一样,一种典型的打扮也代表着一种典型的工作,或者说是审美取向。我们生活中充斥着视觉,视觉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多的一种形象构成,它来得直接霸道,不容置疑,它是最不需要翻译的语言,除了一部分装扮依然需要一点特定的知识,其他都非常容易解读。在穿着上,最有创意的肯定是那些跟舞台表演相关的职业。在生活里,其实就是那些做音乐的朋友。
文学和视觉非常不同,这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一个好的作家或者诗人,一定会重视作品中对视觉的呈现,对物质的描写,比如俄罗斯大师们特别擅长描写大自然,我尤其喜欢看伊万.布宁的短篇小说,里面有对俄罗斯乡村的景色描写,还有对少男少女们的服饰描写。库切在《等待野蛮人》里面反复描写了一段关于孩子们堆雪人的场景,这是一种意象,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如果是梦也肯定是噩梦。在结尾,他又提到了这些堆雪人的孩子。“广场中央一帮孩子在玩堆雪人。我不想惊动他们,却怀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蹚过雪地向他们走去。他们忙着自己手上的事都顾不上瞥我一眼。硕大溜圆的身子已经堆起来了,这会儿他们在滚一个雪球要做雪人的脑袋。”
最后他们终于推成雪人了,有个孩子还给雪人戴上了自己的帽子。
真是个不差的雪人。
一个一流的作家是不会在小说里轻飘飘地安慰人的,请允许我分享一下这本书的最后一段话,纯粹作为一种欣赏:
这不是我梦里所见。就像如今经历的许多事情让我感到很麻木,就像一个迷路很久的人,却还硬着头皮沿着这条可能走向乌有之乡的路一直走下去。
谢谢大家!
还有另一个结尾,当时我没用,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吸收精华,为我所用
无论是写作还是其他创意工作,刚开始肯定是模仿和吸收,过程中是尝试着原创,接下来直到最终,是努力探索和创新。在我需要指引的时候,我喜欢看传记。我喜欢看那些各行各业成功人物的传记,这可以最大程度上了解一个人是如何做到自己领域内最好的程度的。最近奥姆海默的传记电影也快上市了,他的传记我买过,我喜欢一遍遍看自己喜欢的片断,尤其是青少年时间的成长史,只是不同的时候,读的侧重点也不同。现在我重新看,印象很深的是他妻子基蒂也想继续事业但为了家庭没有办法继续发展,她很不快乐。作为女性创作者,当我的女性意识觉醒后,就会更留意书中关于女性的描写。前一阵子我读了一本海外历史学家王赓武回忆录《家园何处是》和《心安即是家》,留意到他的妻子是如何全面地配合他的工作,数次搬家,毫无怨言。没有这样的配合,很难说他是否能够做出这么大的成绩。我同时设想自己是王赓武和他的妻子,在命运选择的关头,该做出何种选择,最利于自己的事业及人生。当然,这种联想让我很累,但作为一个女性,这也是必要的思考。前人很多,我受过的恩惠也很多,从数位文学大师,到小众的摇滚乐队,从经典的电影,再到时装设计师,当然也包括摄影师,画家,艺术家,我感谢他们的艺术创作,丰富了我的人生,给了我艺术的享受,同时也让我的写作更立体,最终,它们都幻化为一个个的具体形象,一个个人,充满喜怒哀乐,在我身边陪伴着我。
最重要的是,生活中那些给我爱的人或事物,我希望围绕在他们身边,即使不能,也希望身边存有他们的照片,每当看到,就会给我美好的感觉。
时间有限,这次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